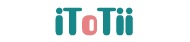初冬的暖阳,透过明净的窗,洒满室内的各个角落,也温暖了床上的他。他刚刚醒来不久,还不能说清楚一整句话,但对于她的名字,却说得清清楚楚。
因为他曾是一位植物人,躺了整整十八年,而他的妻子,也就是身边的她整整陪了他十八年。十八年,不长,转瞬即逝;十八年,也不短,日夜煎熬。
提起这事儿,她的心就刀绞般地疼,她不记得因为这事儿流了多少泪,伤过多少心了。她只知道,他从那一刻起就再没有醒来过,再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
那是十八年前,还在上班途中的他突发脑溢血,昏倒在路上,被路过的好心人送到了医院。而当她听到消息跑来医院的时候,他已经被医生下达了重症通知:出血量已达50,治或不治,一句话!她颤抖的手接过那一纸通知,仿佛握着千斤之重,治,开颅手术,生死未卜;不治,他才四十岁,那么年轻,就等死么?
泪,于那一刻,轰然而下,茫然,无助,心痛,一股脑儿地向她涌来,把她逼到了痛苦和绝望的边缘,进不能,退不忍。然而,当她看到风风火火跑来的女儿,那稚嫩的脸庞和胆怯的眼神,于瞬间让她的意志超乎寻常的坚定。女儿才十岁,还那么小,不能没有爸爸,不能没有这个家。于是她毅然绝然地告诉医生,做手术,治!
她签了字,他也被推上了手术台,手术最终成功取出了脑中於块,即便还存有少量积液,但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然而,最让她意想不到的是,他却在手术之后成了植物人,即使在手术前医生说过可能会有这样的后果,但她在那一刻还是无法接受事实。她征征地站在原地,一天里经受了天堂和地狱般的励练,她的心于瞬间跌落到了谷底。夜,漆黑一片,医生的话还回荡在她的耳畔‘植物人治愈的可能性危忽其危,最好别抱什么希望了吧!’于是,她又一次茫然了。
然而,生活还得继续,女儿是她生活下去的动力和支柱,她不想让女儿失去爸爸,失去这个家,她就要好好地活着,而且让他也好好地活着!于是,她奈于高额的医疗费用,把逐渐恢复好的他接回了家。家里的床不适合他住,况且他高大的身体,她也背不动,便通过熟人打听到一家康复医院,跑去和医院领导好言相说,买回来一张二手的可升降床供他用,这样她照顾起他来就方便得多了。
从那以后,她每天要比平常早起一个小时,抓紧时间洗漱,做好早饭,安顿好孩子,然后照顾床上的他。他不能自动进食,于是她便用粗针管把事先打好的流食推进他的胃里,再为他擦洗身子,以免会生褥疮,而且每天至少三遍,翻身按摩,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程序。就这样,每天下来,她都累得腰酸背痛,手脚发麻,然而她毅然坚持忍耐着,一个信念:相信有一天他会好起来的!
那时候,两家老人也都已年迈,需要照顾,她连个帮手都没有。没办法,为了更好地照顾他,她向单位请求停薪留职,单位领导也知道她的情况,没费任何周折便办了下来。于是,她又在离家较近的地方找了份临时工,至少可以添补些家用,日子就在这种紧张而忙碌的状态下进行着,她也在岁月的磨炼中日渐沧老,眼角过早地爬上了鱼尾纹,那深浅不一的纹路印证了她生活的无奈和沧桑,然而,那一抹坚持与倔强却深深地刻在了她的骨骼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