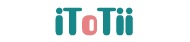文/春杉大道
你知道吃生豆角会中毒的对吧?你看看你做的这豆角熟了么?你想毒死我啊?你想毒死你唯一的宝贝儿子吗?我不想承认,可是这些话的的确确都是出自我口的,年少轻狂,话不过脑,都是我的真实写照,而那一切不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脱口而出的任性矫情都能够清晰的仿佛昨日重现,以前听说过伤害人的话会像一道道伤疤一样刻在别人的心口,纵使时间肯宽容了你,可心头里的疤痕总会留痕,如今回忆起来的时候,我正像是透过一部时光放映机,在看着那段属于我的历史重新点映。
夏日里,餐桌正对着的窗户向房间里头倾倒正午时分一切能够关联起闷热的聒噪声,蝈蝈都被烤得有些沙哑了,相互抽动的柳叶们也只是懒懒散散地发出沙沙沙,偶尔窗前一两个骑车走过的行人,并不经心碾过的石子碎裂的声音里也都包裹着滚烫。
我推开面前的米饭,放下筷子,像是要对母亲做出宣判一样,目光里头当时一定是写满了执拗和自以为的委屈,很混蛋地挑刺,不知道是不是被外面的热气给呛到了,总之,整个人活脱脱地一副“你不重做,我不吃”的神情。然后,我这样僵直地坐着,一脸委屈对着桌上的一盘豆角,而母亲却咧开大嘴笑了。
母亲是这样的,不笑起来看上去温和可亲,可是一旦笑起来就充满了感染力, 许是因为她笑起来并不好看,上下两排牙齿整齐划一地做着阅兵式,许是因为她笑起来声音变了调,又毫无节奏感。总之,任谁听见了她的笑声,原本板着的脸也必将破了功。母亲说,有啥不能吃的,我吃了没事儿啊,那个“啊”字,母亲做了降调处理,这样的话音里多多少少有点心虚的肯定,以及嫌弃我事儿多的成分在其中。
我到最后仍旧没碰筷子,用任性不听劝来表示抗议。家乡那一年的夏天很闷热,但好在是暑假,饿上一顿并不会怎么样,何况下午我就打算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享受一下午的清凉和平日里没看足的电视节目。就这样滤掉了母亲一遍一遍,一轮一轮,从轻声细语到音调提升8、9度的召唤。
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回看总是莫名觉得好气又好笑,气的是那时候的少年啊,你做过多少次这样无聊又轻狂的傻事啊,等着母亲出门上班,饿到后来实在忍受不了,然后形似壮烈地将本不难吃却冷掉的菜,配着电视上的肥皂节目消化进肚,然后等母亲回来关心我吃没吃饭,那时我总是不答。就好像这样做,便可保全了尊严一样,但其实呢,幼稚得很。
不过,那些空掉了的盘子每每都会嘲笑我,只是后来啊,我才开始发现,每一次的任性后头,那冷掉的一盘菜肴里,母亲竟也没怎么吃上几口,原因不是不好吃,而是她知道我会偷偷把它吃掉,却又担心我不够吃。
没吃掉的豆角,却出现在了工作后加班时分的外卖餐盒里,它们油水不多,安静的和身旁的排骨共同枕眠于餐盒中,我咬下了一口,却终究没有办法下咽,敏感的舌头须臾间把我拉回到了那个夜晚,舌尖上缠绕出植物刚刚从田间采摘而来的新鲜感,每一口咬下去豆角的汁水里多多少少掺杂出些青绿的口感,就仿佛看到了竹篓里裹着霜露的扁豆的样子,从味蕾中慢慢被描画开了。
“晚上吃炝炒豆角丝行不行?”厨房里,母亲的声音飘了出来。我扯着嗓子和抽油烟机的轰鸣声搏斗,一个字“行”,说了3遍,然后我就又沉醉在电视节目当中去了。那个时候上学离家不远,你也不会知道有一天会走过那么多地方,见识到那么多风光,结交到那么多可能并不能长存的所谓友谊,你也不会知道有一天你离家遥远,曾经叛逆简单的愤怒咆哮,无理取闹,头脑发热,有一天都会回来的,只是他们化作了一缕缕浓烈的乡愁和思念。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itotii » 珍惜和你爱的人吃的每一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