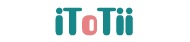文/anymirror
留学第一年的十二月,是留学生纷纷斩断情根的一个月。只怪那糟糕的天气,只怪那彻骨的寒冷,让一切都显得岌岌可危。落叶乔木掉光了叶子,动物不再肆意活动,天空像是一张睡意昏沉的脸。很多人从国内的恋人那里再难获得一丝温暖,于是攒足了勇气,掐灭了异地恋最后一簇奄奄一息的火苗。
这天我旁听了室友的分手电话。她去意已决地回答对方的各种提问:怎么会,为什么,因为谁。那个电话很长,我纠结在一旁,一直想要打断他们去劝说些什么,但总也找不到强有力的说辞。她想要留在这边三到五年,对方却因为身份问题永远被锁在了国内。她推崇这边的自由和烂漫。对方却想要一个稳妥而安全的结婚对象。那摸索不到的未来和那难以名状的距离,明显地横亘在他们中间。我也随之烦恼起来。从她的房间退出来后,我拨通了自己男友的电话,问他:“阿城,你还好吗?”
他在离我有十二小时时差的地方,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正值午休时间,他没有随着人潮涌向写字楼底层的食堂,而是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说:“挺好的呀,怎么了?你声音怎么不对?”
“没事,正好到了今天要给你打电话的点了,就拨过去了。有没有什么新鲜事?”
他熟悉的话音响起:“老样子。码农的一天,除了写代码就是在准备写代码。还是听你说说你那边的事吧。”
我和他说起我的日常,今天马马虎虎地回答了老师的提问,今天照着手机里的菜谱做了罗宋汤,今天这边已经零下十度了。都是一些无聊小事,而且越说越无聊。他耐心地听,不曾打断我。说了半个钟头,我自己停了下来:“你再不去食堂,该没有饭了。”
直到挂断电话,也没有跟他提半句室友异地恋告终的事,否则这一通电话绝不止半个钟头,他可能在电话那头,进行各种脑补,哭也要哭半个钟头。
阿城就是这样的一个敏感的男生。
阿城与我早年相识,他是站在我身旁的不露声色的容器。沉默寡言如他,让人不知他心里藏着的是温吞的水还是浓烈的酒。与他在一起时,往往是我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他总是鼓励我多说,他负责当我各种情绪的收纳器。有时我身陷困境无从选择,他提醒我:“要是过去的你可不会这样想。你不是说过……”原来他用心铭记了我的每一句话。当我发现这就是爱时,已经为时已晚。我们改变了关系成为了恋人,但在两个月后,我收到美国一所研究生院校的录取通知书。那是我备考两年才拿到的录取。与之相比,两个月明显输给了两年。
两个月让感情升温,而后又有一个接一个的两个月在消散感情的余温。来到异国的第四个月,十二月,我在做实验时因为手套滑落而被烫伤,我不免俗地,感受到了时间和距离带给人的无力感。手腕上的伤口从破裂到结疤不过是几秒钟的事,痛觉从神经末梢传递到大脑也不过跨越了几米的距离。而在这几秒钟内,阿城在几米之外的彼岸?
我忍着疼痛走到学校的医务室,不巧碰上医务室关门。校外的医院,必须托有车的朋友带我前往。实在是太麻烦了,还不如任其自生自灭。我回到了公寓。但在公寓里无所事事的我,无法对这道伤疤不闻不问。它如此丑陋,像一条人见人憎的虫,万一敷药晚了无法治愈该怎么办?我发了一条信息给阿城:“我的手腕被烫伤了。想到将来在婚礼上,我伸出左手准备带婚戒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我手上的疤痕吸引走了,那太可怕了!”阿城尚在睡梦中,对我的恐慌浑然不觉。
那一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鲜少在留学生QQ群里发言的我,开始向人求助了:“请问谁有治疗烫伤的药?”
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了和我同病相怜的迅十。
迅十租住的公寓就在我公寓的前一栋。从我的窗口往外望去,他的窗口在婆娑的树影之后透着并不张扬的橘色光芒。原来是住在那里的一名留学生,以前应该在同一个车站打过照面。去见迅十之前,我试图在记忆里检索他的形象。无果。应该不是男神级别的人物,否则过去肯定多看了几眼,也不会觉得他的名字这般陌生。这么一想,我收起了我的惴惴不安。像见一个老朋友一样,按响了迅十的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