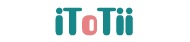和她相识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整家工厂都是背包客的聚集地,他们从巴西,韩国,阿根廷,马来西亚等遥远的国家来,到这里赚旅费,交朋友,谈恋爱,做足一两个月的工便离开,并不做什么用心的停留。
然而我和她不是。
她叫萨奇,清瘦,个子高,一头长发,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活得干净漂亮的姑娘。几年前从日本漂到澳洲,扔掉做厨师的帽子,在珀斯停留两年整,却偏偏活成了不爱热闹的人。
那之后她来到新西兰,爱上了这里的纯净和安逸。她和我讲自己过去的历史,而后感慨,“真想留在这里,一辈子哪也不去。”
我在她对面的流水线打包,哈欠连天地回复着,“是啊,就是赚起钱来太费力了!”流水线督导经过我,戳了我的腰,告诉我“快点做工,不要这么多话。”
那是我刚刚搬到陶朗加时的状态,顶着各方压力逃出了奥克兰,想迅速建立生活,从哪里开始都可以。
陶朗加一向以“十纽币陶朗加”著称,一直以来挑战着全国最低工资的底线,而人们从不抗议,是因为这里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常常在临近城市狂风暴雨时,偏偏这里阳光明媚,像是暴风之眼。
这是四季度假的天堂,但凡决心居住在此的人必定拿着真金和白银,而那些贫穷的人们,东做一点工,西做一点工。
虽生活捉襟见肘,但只要每日踏着朝霞出门再拥着晚霞回家,看了一抹世间不多得的美景,大概也就抵消了身体的疲惫。
像我做工的工厂有数处,只要你有手有脚没有钱,他们的大门就常年向你敞开着。我每天早上出现在工厂里,听那些马上要离开的工友们说“攒好去东南亚旅行的钱啦”或者“下个月要去斐济”,我的心慢了半拍,手也停下来,眼睛撞上督导,那张脸饱受生活摧残的脸又开始出现了咒骂的前奏。
“这就是我要的生活?”我跟对面的萨奇说话,带着将要步入二十六岁的恐慌。
我和这生活之间隔了一层雾,很久都想不通未来里,我是一心工作,还是辞职写作,是自创营生,还是埋头苦干,是回国去繁华的日子里,还是继续留在这里过放羊般的生活?
说罢,我看见她眼角出现的细纹,猜测着她的年龄。
萨奇说,“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就一直走,别有那么多顾虑。”
末了,她看穿我的眼神,告诉我,“你看,我三十一岁了,长大没那么可怕。”
三十一岁的单身姑娘在我的家乡会有怎样的体验?
我的国内朋友们从二十五岁开始已经有了嫁人生子的准备,听说那些三十几岁还不着急结婚的都成了“慌张的剩女”。我们一路被劫持着,读书工作嫁人生子,旁人都给出一套“最应该”的版本,踏出和别人一样的步调,这才是最安全的打算。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itotii » 任她去吧,毕竟她单身也美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