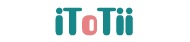她是他母亲同事的女儿。那年,她来他家时,只有八岁,他也八岁。他被母亲屈辱地拽过来和她比身高。一比,她高出他整整半个头。她腿长,经常在门前和他的姐姐们跳皮筋。休息时,她骄傲地扬着下巴,踮着脚尖。她母亲说她在少年宫学芭蕾,跳《天鹅湖》,舞蹈老师看中了她一双修长的腿。
他矮矮的、圆圆的,被太阳晒得很黑。她便跟着他的姐姐们一道,喊他“冬瓜”。那时的他也有自尊,觉得自己被羞辱了,于是,心里就想:黄毛丫头,一脸雀斑,丑得很;腿长得蚂蚱腿似的,好看吗?想到这一点,他幸灾乐祸地笑了—在恶作剧的游戏里,他经常折断蚂蚱的腿。
十年后,他去北方读一所大学。其时,他已高大英俊,内心充满骄傲。一次,母亲从城里同事家回来,告诉他,女大十八变,那小女孩已出落得美丽动人了,现在已经是小学教师,教音乐和舞蹈。他心中一动,还是淡淡一笑:是吗?
母亲交给他一封信和一盒磁带,是她让他母亲转交给他的。信里,她说,她很后悔当年喊他“冬瓜”。信封里夹了几张照片,是她在市里舞蹈大赛获奖的照片,照片中的她,修长挺拔,像一棵高高的白杨树。
他想起往事,淡淡一笑。信,最终被留在抽屉里,磁带被带到学校。那是童安格的专辑,通过磁带,他学会了那首《午夜的收音机》,没事就哼上几句“……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又是二十年过去,他已分配到家乡的这座城市工作多年。一次偶然的聚会,主人介绍他与她认识。彼此的眼眸中泛起似曾相识的记忆。他惊异于她的变化。一袭黑纱,一张洁白的脸,异常的忧郁和美丽。不变的,是她优雅的脖子和扬起的下巴。
聚会结束时,主人才跟他说起她的变故。这时,她已经到了人流如梭的大街。
他飞奔着冲了出去,寻找她。她停住了,平静地朝着他微笑。她比他,矮了许多。
俯下身躯,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动作——单膝跪地,侧过脸贴着她的长腿。他感受到的是金属支架的冰凉。泪,流了下来。时光仿佛在那低头的一瞬轮回,他依稀想起,从八岁那年以后,梦里常常出现一个影子,高高扬起下巴,踮起脚尖……
时光如梦,他看着她。他只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一直想看你跳芭蕾。
三十年后的相见,她那双跳《天鹅湖》的长腿,在一次带学生春游回来的路上,被一辆狂奔的汽车夺走,换回了两个孩子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