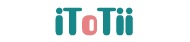八娘15岁那一年,一个好心的守夜人把她领进我祖父的家里来了,因为我八伯有眼疾,30大几也没说上个女人。那守夜人一进门,讨一口清水喝了,然后一抹嘴,说:成不成,花好月圆不,就听老八(乳名)一声哼叽呢?八伯刚起炕,他在松花江上打了三天三夜的鱼了,腰也直不起,眼可能还花着吧,所以打眼一瞅,有送媳妇的,就一个字:中咧。
这样,我们的八娘就得以在祖父那套还算说得过去的灰门大院里落脚了。她那天真是笑得痛快,却不好看,而是比哭还难看。人要真动感情,那脸面会很不受看的,不管是哭还是笑。
等八娘正式嫁了八伯,喜酒喝过了喜烟抽过了。八伯缓过劲儿来了,他嫌起八娘的丑脸了。嫌的方式有二:一是分被窝睡觉,二是他到江边打鱼成年累月不着家,把八娘搁在灰院里晒鱼干。但八娘根本不理会这些,有吃有喝有地方睡觉,她已经烧高香了,假如八伯再对她好,那对她等于是奢求。所以,她每天乐不可支地忙东忙西,对谁都笑脸相迎。那时,祖父家一大家十几口人并不富裕,所有的人家的日子也都相差无几,老张家比老李家过得牛气,也可能就因为老张家的干鱼晒得比老李家多那么百十来斤而已。所以,八娘的到来使祖父家的鱼干晒得超过整条街,外人夸奖,祖父就高兴。他私下里到江沿找过八伯几次,胡子抖颤着也骂过的,祖父说:“能挣会花,不如会算计。八娘是个小金斗,你一定要对她好。”八伯被祖父扯回来,也只是暂住几天便又一走了之。八娘后来有了我大哥松,便不再在意八伯的去留,祖父一想上江边,八娘就找茬劝住他,说:“捕鱼也是为家,不愿回就不回吧。”祖父就长叹一声,把一瓶烧酒托人捎给八伯便做罢。
祖父好好的,突然有一天便心脏病发作,没救过来,走了。祖母一急,也走了。大灰院的天眼瞅着塌了,大伯又远在新疆贩鱼。八伯原本就是个没有主意的人,跑进家门一看,抱住头只管借酒浇愁了。一大摊子的巨细呼啦落到了八娘身上,她哭过了笑过了病过了死过了,好几个来回,她把整个家的担子担在了肩上。她先是打发八伯回到江边捕鱼,又托人写了封长信给新疆的大伯希望他回来收拾家族河山。信如石沉大海,倒是八伯扎根江边的劲头更足了,不叫绝不回家。八娘带着5个小叔一个小姑,还有松哥,便开始挑摊过起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