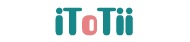在远走他乡前,我是一个从不怕寒冷的东北孩子。我的冬天,是降临在妈织的毛线手套和爸做的白菜炖豆腐里的,我早已习惯他们替我把这厚重的严寒挡在窗外,让我在天然冰箱般的城市里也时刻置身于23度的温暖中。
可是那远行的一年却让我发现,奥克兰不一样,那是离开家的地球另一端,它的冬天是突然的,肃杀的,随着一阵冷风铺面而来的。这里不是家乡,没人给这可怖的季节添点温情的味道。
我至今可以无比清晰地还原那个傍晚。我刚刚结束在亚洲超市里一天的工作,神色疲惫地走到公交车站。这是我来到国外的第一份工作,可那每小时十纽币的薪水让我开心不起来,我就像是挨了成人世界里的第一记闷棍,那一刻我的心里只有两种绝望的情绪相互交替着,一种,是为一份站了整十个小时的“底层”工作,另一种,是刚刚错过了六点十分的那趟公交车。我坐在公交站的长椅上,几乎要哭出来,这下一辆不知何时才来的车,就让我像“等待戈多”那般无望。天就这样暗下去了,不一会就黑了整个头顶,一阵风吹进了我单薄的衣服里,你看,一个称不上是故乡的地方永远冷漠,这强盗般的冬天也来了。
这时我的身旁啪唧坐下一个金色头发的小妞,她动作大大的,毫不客气,有点天真的男孩子气,一双蓝眼珠也毫不惧生地看向我,“你好啊!”
我低声地回应,“你好。”我尽量避开她的眼睛,坏情绪让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话。
她却满是聊天的兴致,白皙的手指指向不远处的灯光,“我刚刚下班,你看,那就是我工作的餐厅!”我的眼睛看过去,那是一家典型的洋餐馆,以“繁忙”而著名,常常到凌晨还灯火通明。我不禁多看了她一眼,她大概和我同岁,显老的白人基因让她的眼角有了两道浅浅的皱纹,她的鼻子冻得通红,黑眼圈有点严重,但那眼神里却没有半点的疲惫。
我依旧心思沉沉地说,“哦,那里一定很忙吧?我也刚刚下班,只希望这公交车快一点来,你我就可以早一点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