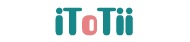文/落叶无声
祭祖
遥遥的,穿过茫茫无际的草原,是高山,穿过高山,便不知再有没有路了。爹爹总说,一路向东,在日光最浓的地方,有红砖碧瓦的宫墙,琉璃翠珠雕饰的殿宇,屋檐高啄的楼阁,成百上千根圆柱上都雕饰着腾云驾雾的青龙,层层的石阶,顶端坐着身披黄袍的君王,那才是家乡—长安,只是念君从未走出过这片土地,这片生她养她却不能叫故乡的地方。后来记事了,她才知道这是两个民族,他们流着不同的血,就像水与火一般,永不可相溶。
“你爹为什么总是不让你出来玩?”
念君赶着羊群与路绍不期而遇。
“我要温习《诗》《书》。”
“温习《诗》《书》?一定没有骑着马儿在草原上奔跑有趣。”
“可爹爹说,我是汉家女子,便要知书达理德才兼备。”
“我娘就从不教我这些。”
念君早就听别人说过,路绍的娘是个高大壮实的匈奴女人,只因在危难之中救过路伯伯的性命,日后便有了路绍。有几次牧羊,经过路绍家的穹庐(穹庐:匈奴人住的地方)时,那个匈奴女人都用手比划着,执意邀请念君去做客,可是爹爹再三嘱咐过,不准靠近匈奴人,于是她都挣扎掉她粗糙的大手,慌忙跑开了。
汉历三月初三。
天还未大亮,爹爹已备好了酒水,换上一袭黑色衣袍,人陡然精神了许多,他一脸正气,连目光中也多了几分炯炯之色。记忆里,年年如此,也只有这一日,爹爹才会去次不同寻常,因为这一日是上巳节,千万汉族人祭祖拜天的日子。
第一缕晨光洒在草原上时,山坡上聚集了所有留在匈奴的汉使他们都同爹爹一般着装,均面色严肃。念君作为女子,跪在队伍的最后,穿过人群,她寻到了路伯伯沧桑的背影,未曾看见路绍,对于这种庄重的汉族仪式,路绍自然是不被允许参加的。
入夜后,草原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篝火,今夜是匈奴和大宛和亲的庆祝宴会,匈奴单于的女儿要远嫁大宛国王子,单于特别下令,今夜从奴隶到俘虏都不用干活了,一起狂欢舞蹈。
穹庐外隐约传来清脆的乐器击打声,或许还有异域的歌声。念君手捧《诗经》在昏暗的牛油灯下打盹儿,也不知爹爹去了哪里,总之,他临走前万般叮咛,不准去参加匈奴人的宴会。
念君放下书,掀开帘子走出穹庐,远处的篝火连成了片,歌声弥漫在整个草原的夜空中。这么多年,她从未参加过什么匈奴人的宴会,每次都是听路绍娓娓道来,她是羡慕过,但她也同样理解爹爹此番做法的用意,爹爹要她记住,她是一个汉人,时刻都记住,汉人的思想和习惯才是在她心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所以,她从不怪他的苛责。
“念君,你爹又不让你去参加宴会?”路绍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夜幕中。
“嗯,你怎么在这?”
“你看这是什么?”路绍神秘的从衣襟中掏出一包用手绢包裹的东西,缓缓打开。
“桃仁酥?”念君欣喜地接过来,咬了一大口在嘴里“你从哪弄的?”
“这你就别管了。慢点,没人和你抢。”
路绍在念君身边坐下来。
“念君,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离开匈奴回到汉朝去?”
“爹爹说了,我们迟早会回去的。”
路绍的目光黯淡了下去。
谈论到路绍身份这个尴尬的问题,两人都沉默了。念君只是小心翼翼的咀嚼着嘴里的食物,看着他沉默不语,今夜的草原,从未想此刻这般宁静。
北湖的牧羊人
念君原本以为,和爹爹所在的地方便是极苦极寒的地方了,没想到继续向北走,还有人烟。
跟着爹爹行走了约莫有一天的时间,因为是私自离开的,要躲避匈奴人的视线,他们也没敢骑马,从早上天没亮就动身,直到现在晚霞染红天际,才隐约看见前方有一片瓦蓝色的湖,夕阳中依稀有在湖畔挥鞭赶着一群羊。
霞光有些刺眼,待念君睁开眼时,爹爹已经抛下她独自前去跪拜那牧羊人。
“念君,快过来,拜见苏大人。”
苏大人,他便是爹爹常提起的苏武大人了。当年苏武大人受尽匈奴人折磨也不肯受降的事爹爹早已向她讲过百遍,今日真是难得一见。
“念君见过苏大人。”
“快起来吧,都长这么大了”苏大人慈爱的抚摸着她的头,“我的三个孩子,若安好,便也这么大了。”他重重的叹息,目光飘向遥远的东方,念君怎会不知那是长安的方向?那里有雄伟的皇城,有他俯身跪拜的至高无上的君主。
“大人,让您在此地受苦了。”
“无碍的,我日日牧羊,倒也不觉得日子难过,除了这里人烟稀少,有些寂寞罢了。”
爹爹和苏大人走在前方闲谈着。念君见苏大人背在身后的双手紧握着一根手杖,上面节旄尽落,汉式的花纹清晰可辨。
爹爹和苏大人兴许是数年不见,长谈至深夜。念君环抱双臂在穹庐对面的少坡上看星子。她记得路绍说过“所有离开的人,都在天上变成了星子”,那么娘亲呢?她在天上,定能看见长安吧。
天刚有了一丝微光,便隐隐听见有马的嘶号声。
“念君,快些起来。”爹爹匆忙催促道。
苏大人神色慌张的掀帘而入。
“常惠,先带念君暂且避一避,匈奴人来了。”
“大人,我们在此只怕是要给你多添麻烦,不如趁现在返回吧。”
“万万不可,我们在高地,现在出去只怕是要和匈奴人打个照面了,到时候更不好收拾。”
“那,这可如何是好。”
“莫慌,穹庐后有一口大水缸,尚未盛水,你和念君躲在里面,匈奴人由我来应付便是了。”
念君和爹爹刚躲进水缸,收拾妥当,便听见了穹庐前淅淅沥沥的兵器和马鞍的碰撞声。
一个匈奴人大声道:“苏武何在?”
“在下方才牧羊归来,不知将军突然来访,有失远迎,还望将军恕罪。”是苏大人临危不乱的声音。
那匈奴人得寸进尺,“为何不讲匈奴语?”
“在下是汉人。”
那人冷哼一声,“汉人又为何会在我匈奴的土地上?”
“匈奴人背信弃义。”
“胡说”那人声音陡然增高,随后还有大刀出鞘的声音。
念君吓得瞪圆了双眼,若不是被爹爹紧紧的捂着嘴,她定要惊呼出声。
“你以为汉朝的皇帝还在乎你们这些人的命,我单于好心劝降,留你活到今日,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本就是大汉朝的臣子,为国家而死又有何怨言?”字字掷地有声,不卑不吭。
“好好,我今日就杀你,以你的首级祭奠我匈奴大军。”
“将军您忘了,单于特别交代过,苏武要留活的。”有人急忙劝阻。
似乎僵持了很久。
“哼”匈奴将军将刀狠狠的插回刀鞘中。一群人浩浩荡荡的离去,“�N�N�N”的马蹄声渐远,草原上又重新恢复了平日里的宁静。
好生惊险的场景,念君的心从胸膛跳到了嗓子眼,然苏大人平静的脸庞,让念君第一次觉得。这个看似瘦小的身体上,蕴藏着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量,撑起了整个大汉王朝的尊严。
此次从北湖回来,有惊无险。念君时常会回忆起那次在北湖的遭遇,以及苏大人面对死亡时波澜不惊的面容,只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去拜访过。
与李陵初见
那日的风极大,川地四下平坦,本是一年四季风都刮不停。记忆中,这里少有不刮风的日子,头顶的阳光再明媚,风也会卷起衣角沙沙作响。念君喜欢这里不染杂尘的天空,却不喜这风,十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这风吹在他身上像利剑一样划破她稚嫩的肌肤。爹爹说,因为那不是家乡的风,不懂离乡的情,也许吧。那个被叫做长安的地方,那个无数次出现在梦中的地方,才应该是他们真正的归宿吧。
“�N�N�N”的马蹄声从远方响起,念君把自己藏进高高的草丛中。
“小孩,你叫什么名字?”念君听得懂,骑在马上的人在用匈奴语问话。
“我叫常思,字念君”念君朗声道。
“你会说中原话?”来人把马拴在一边,走到念君面前。
此人一身凛然之气,腰间配有汉人的长剑,两条剑英眉向上扬起,左不过三十岁出头,俨然一副中原将军的风姿。
“我是汉人,自然说中原话,可你为汉人,却为何要讲匈奴话?”念君咄咄逼人。爹爹说过,中原话是每个中原人嵌进骨血的语言,任何时候都不可抛弃。
来人不怒反笑,“好生有趣的小女娃,中原人都学儒家文化,而儒学中长幼尊卑之礼则为大礼,若论起年岁,我要比你长许多吧。”
“你不说中原话,算不得汉人。”
“可圣人孔子有规定过,这礼有种族之别么?”此人脸上的笑意更浓,英挺的眉毛向上挑起。
念君站起来,才觉他如此高大,倏地脸一红,反身跑掉了。爹爹常教导她,汉家女子要含蓄,不可像匈奴女子般狂野粗俗,见到陌生男子要自持。
夜里,王伯伯来访,念君在穹庐外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常兄,李将军今日可有拜访你?”
“哼,他来做什么,既然投了匈奴,就是我们的敌人。”
“哎,李将军是个人才,他头像也实属被逼无奈。”
“被逼无奈?被逼无奈就可以投降匈奴?被逼无奈就可以叛军叛国?再大的冤,再大的孽也大不过背国弃家。”
念君第一次见爹爹如此恼怒,就是从前面对匈奴人时,爹爹也只是冷漠不语。是汉人,又是将军,那今日巧遇的英气男子定是李陵了,可是,他竟然投了降,那样一个骨血里充满傲气的男子,他竟然是一个叛国叛家的人,他在日光下熠熠生辉的战甲,仿佛刺痛了她的心。
深夜,爹爹来到她的穹庐中,念君把脸转向里面,佯装睡熟。她感觉到爹爹长满茧子的大手轻轻抚过她的脸庞,扎扎的,痒痒的。
爹爹长叹了一口气道:“念君啊念君,你可知爹为何要给你取此名字,常思国,念吾君,若无缘,归故里,此一生,定不忘,魂归处,是故乡,魂归处,是故乡啊。”
爹爹的声音渐渐远去,回荡在草原凄冷的夜空:
常思国,念吾君,魂归处,是故乡,
常思国,念吾君,魂归处,是故乡。
十五岁生辰
天汉十年,腊月初一。
爹爹说,这时到了长安最冷的时候,但也是长安城最热闹的时候。因为除夕夜就要来了,中原人普天同庆的节日岁旦(岁旦:汉武帝时期春节的称呼)就要到了,腊月初一这一天,正好是念君的生辰。
冬季的川上真冷,连长着浓密皮毛的牛羊都冷得哆嗦发抖。念君没有太多御寒的衣物,匈奴人将他们流放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替他们放牧,每隔三五个月来问一次话。
念君套上一件破旧的外衫,这件外衫已经穿了好几年,上面布满了爹爹粗糙的针脚。
“念君,跟爹爹来。”
爹爹带她到穹庐中,从绣有汉式花纹的箱子里寻出一个包裹给她,“打开看看,爹爹对不住你,没有什么可以送你作为生辰之礼。”
念君解开系的精致的蝴蝶扣,里面是一身衣裙,这衣裙用手摸上去丝丝滑滑的,仿佛在手上钻了流沙一般柔软,长这么大,念君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衣物。
“念君,这便是中原产的丝绸,这是你娘留下的,现如今,爹爹就把它当做十五岁的生辰之礼赠与你。”
念君诧异,这如落日彩霞般的衣裳,竟是来自她遥远的家乡。
“在我被扣留匈奴的第二年,你娘带着刚刚六岁的你,从千里外的长安来到这苦寒之地,长途奔波的劳累再加上条件的艰苦,落下了一身的病,卧床再也没有起来过。”
爹爹抚摸着他常抱在怀里的铁匣子,盖上的一层朱砂已经尽落。
“你8岁那年,她因病长期无法医治而去了。你娘临走前,爹应允她,若此生再也回不了长安,便让她的尸骨随风而去,若得幸回到长安,便叫她入土为安。我回不去,不是还有我的子子孙孙吗,我们就一代一代的走下去,只要不到长安,我们就一直走下去。”
爹爹伸出双臂将她揽入了怀中。爹爹实在是太消瘦了,宽大的衣袍仿佛只包裹了他的一副骨头。
“念君。你今天这身一群真是好。”
“这是我爹爹送我的十五岁生辰之礼。”念君挥着长长的牧鞭,赶着羊群欢快的奔跑。
“我也有东西送予你。”路绍在身后追赶。
“你先闭上眼,可好?”
念君猜不出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依了。
颈部有些许清凉的感觉,念君的目光定格在颈上的项链,一颗颗透亮的琥珀石被打造成精致的形状串在一起,长这么大,念君没见过什么首饰,如此美丽的,还是第一件。
“这,这是我娘留下的,我,我一个汉字,留着也没什么用处。”念君头一回见路绍连说起话来都不利索了。
念君“噗嗤”一下笑出了声。
路绍的脸上飞快窜上两抹红云。
“路绍,我爹说,家乡的女子,到了十五岁便是出阁的年龄了。”话刚一出口,念君的脸也飞快的烧了起来。她是赶着羊群逃回穹庐的,殊不知身后的少年在夕阳下展开了笑颜。
十五岁,不是普普通通的生辰,所以她们的小穹庐中今夜挤满了客人,全部都是留在匈奴的汉人,其中自然不乏路伯伯。
没有什么好菜,只有几坛爹爹自己酿的酒,平日里舍不得喝,今天全都拿出来招待宾客,也算是一顿难得的酒席了。
“常兄,女儿家过了十五岁就不小了,你可考虑过念君的终身大事?”
听到有人提及自己,念君颔首。路绍今夜没来,思及傍晚的事,念君的脸又不加节制的烧了起来。
“不如,今夜我们大家一起做个主,为念君挑个好郎君,不知常兄意下如何?”
念君偷窥爹爹,只见他一杯一杯的饮酒,不做言语。
“我看论年龄与长相,路兄之子路绍都是上上之选了。”
有人立刻附和上来,大帐内顿时吵作一片。
念君不敢再抬头看爹爹和路伯伯。
“简直是胡闹!”爹爹将酒杯重重的砸在木桌上,“路绍有半个匈奴人的血统,从小玩到大可以,但我常思之女决不可嫁予人为妻。”
帐内因爹爹的一席话安静了下来。
念君的心也随之冷了下去,早就猜到是这样的结果,不是么?
“爹爹,你醉了,我扶你去休息吧。”念君边向来人陪不是,一边收拾残局。好好地一顿酒席,便这样惨淡的收场。
不过半柱香的功夫,人便都走光了,路伯伯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盯着念君颈上的项链良久,才道了一句“照顾好你爹爹”便隐没在草原辽源的夜色中。
安顿好睡熟的爹爹后,念君坐在铜镜前看见了自己空荡荡的颈部,带过琥珀项链的地方还留有些许余温。此生的缘分已尽,此生的情也只剩这点温度可以回忆。她让路伯伯带回去的信和物,还望路绍看过后不再有所怨恨。
我意所属,父命难为,君若解我,便知我情,纵是此生无缘,愿与君,长相忆。
罢了,老天自有安排。
告别
风吹过川上,草绿了一季又一季,岁月往复,催人易老。
天汉十三年,三月末,春风日过后,正是草场疯长的日子,然一个消息迅速如瘟疫般在草原上传开。
汉朝的皇帝驾崩了,武帝驾崩了。
爹爹听后,先是静默良久,后面向东方,长跪不起,“国难啊!这是国难。”浑浊的泪水自眼角流出。
念君很想哭,却掉不出眼泪,因为她尚不明白,那个素未谋面,高坐于龙椅之上俯视九天的男子,于她,于爹爹,于天下的黎民百姓究竟意味着什么。
新帝很快登基,大赦天下。而对于他们这些在草原上苦苦守望了几十年的汉人,一切都没变,日复一日,都是对故乡的思念。
始元四年春。
匈奴再次与汉朝开战,大败而归,西迁几百余里,同年秋,匈奴西征。
凭着感觉,念君觉得距离她们回乡的日子不远了。自打她有记忆起,匈奴和汉朝的战争向来是以败居多,匈奴这个民族在一年年的衰弱下去,武帝的死,似乎并未使这一情况好转,连年的天灾,让匈奴损失了大量的牛羊,战斗力大不如从前。
“�N�N�N”熟悉的马蹄声,一如从前。
“我第一次见你时,你还是个伶牙俐齿的小姑娘呢,一转眼便这么大了。”
在匈奴的几年,李陵没有了初来时中原人身上的儒雅之气,多了几分匈奴人的粗犷,而依然不变的是他英挺的双眉间向上扬起的傲然之气,与那年初见时一模一样。
“念君,你跟他们不一样,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并没有那么排斥我,我能从你的眼神中感觉到。”
“为什么投降匈奴?”念君想是被他言重了,第一次见这个英气男子,念君便念念不忘于他身上那股逼人的凛然之气,明明是那样一个铮铮傲骨之人,为何……几年来,她一直想寻机会要个答案。
“人在很多时候做的选择都是万不得已的,若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也不会选择如今的路。”
他的这一句话,若是解释,念君信了。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帮忙的。”他从衣襟中拿出一个绢帛,“这是一份家书,我料你们就快回长安了,我听单于说,皇上已经着手与匈奴王庭交涉此事了,如果”他顿了顿。
念君抬眼看见他孤独的背影伫立在阳光下。
“如果李家还有侥幸活着的人,请你务必将这封家书交予他。”
念君静静与他对视半晌,伸出手接下了僵立在半空中的绢帛。爹爹若是知道了,只怕是要不认她这个女儿了。
“常思姑娘的恩情,我李某此生无以为报。”他双手抱拳,垂下了头。
“李将军,你真的,不想再回去看看嘛?”
“回不去了,只怕是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品长安的美酒,嗅到三月的桃花香了。念君,长安是个好地方,如果真的回去了,就在十五的月下敬我一杯桂花酒,可好?”
“一言为定。”
“我要走了,明日便随大军西征。”
“去哪儿?”
“不知道,一路向西,活着走到哪算哪吧!”他跨上马背“此生定是无缘再见了,保重。”
“驾。”马在风中嘶号着扬起前蹄,向夕阳的方向奔去。
念君用尽全身的力气在风中呼喊,
“保重,保重……”
她只记得马背上的人回了头,在夕阳中微笑,直到从她的视线中消失。念君捧起手中的绢帛,立马有水滴在上面,她才感觉到,自己是哭了,为那样一个傲然伟岸的男子。
如果老天有眼,请保佑他,平安归来。
归乡
李陵说的果然不错,长安又来了一批人,据说与匈奴约好,回长安,指日可待了。
动身回长安的前一夜,爹爹怀抱装有娘骨灰的盒子说了一宿的话,而念君也望着草原分外明亮的月,悲喜交加。
路绍最后没有跟路伯伯回长安。念君知道,路绍和自己不同,他对匈奴人是有感情的,因为他的身上流着一半匈奴人的血,而且他的娘亲也长眠于这片土地下,只是从此以后,他便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独自生活。临行前,路绍送她很远,最终还是把琥珀项链戴在了念君的脖子上,这一次,爹爹也没有阻拦,正如他在信中道:自此一别,相间无期,这也只是最后的念想了。
除了路绍,念君在匈奴无牵无挂,只有那个在异国他乡征战的人,如今不知道是生是死。
后记
在马蹄翻起的滚滚尘土之中,城门缓缓打开,或许是梦过了太多次,如果这次也是一个梦,念君情缘一世不醒。如爹爹所说,连故乡的风都是软的,还夹杂着不知名的花香,比任何一场梦都令人沉醉。
长安啊,长安,这便是故乡吧!